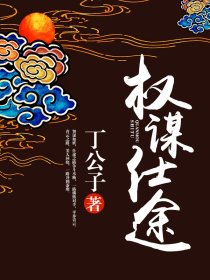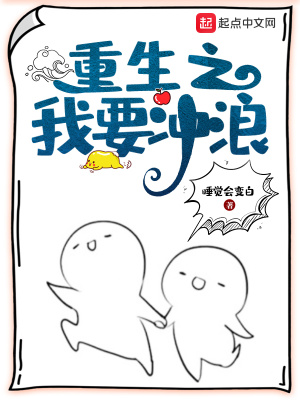倚天中文网>那些年我和夫郎的种田生活 > 3、第 3 章(第2页)
3、第 3 章(第2页)
姜家父母和姜辛夷自不必说。
在姜辛夷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。
大妹,姜慕荷,十七岁,去年嫁去了离这里有五里地远的曹家沟。
大弟,姜苏木,十五岁,在镇上一家学堂读书。
小妹,姜紫芙,七岁,在家跟着姜辛夷学医。
按理说,姜辛夷是大哥,又对底下的弟弟妹妹照顾颇多,一家人该很亲近他才是。
但从姜家父母到姜紫芙对姜辛夷的态度都是敬重有余而亲热不足。
还有一点很奇怪,明明姜父姜母都知道,他不是姜辛夷的未婚夫,可他们竟然问也不问一声。
好像就这么默认了。
对亲儿子的婚事,这么草率的吗?
就算知道,这桩亲是假的,那也不至于一点都不在意吧?
“……”
说不在意那是假的,只是他们没资格在意。
姜辛夷不是他俩亲生的孩子,而是他们十五年前从府城赎身回乡途中,主动找上门来,要拜他们为父为母的孩童。
这些年过去,当初那个比乞丐还要凄惨的孩童已经长成了成熟稳重的大人,麻烦也接踵而至。
村里人频繁地向姜辛夷说媒,偏姜辛夷一个也看不上,差点说出这辈子也不成婚之类的话。
世界上不成婚的只有和尚、尼姑,道士,老光棍四种人,他家木兰如此拔萃,怎能不成亲呢。
姜家父母实在没法子,只得拿他们当年在府城给人当丫鬟仆人的事说事,编撰他们在府城给姜辛夷定过一门亲,只是那家人因为灾荒搬走了,暂时断了联系。
要是草草给姜辛夷说了人家,以后人家找上门来,没法交代。
徐鹿鸣一上门,姜家父母从地里回来的时候,就暗中商量过,不管姜辛夷带回来的这个人是人是鬼,只要他是姜辛夷承认的未婚夫,他俩就得把这个事给坐实了。
这会儿见过人了,他俩找了个借口在主屋碰了个头。
赵二娘问:“当家的,你觉得这孩子怎样,配得上咱家木兰不。”
姜大年坐在桌角,一脸无奈:“配不得配得上,也不是咱俩说了算的。”
赵二娘不服气:“怎麽就不算了,好歹也是我们从小养到大的,不是亲生的也胜是亲生的了。”
姜大年默了默:“这孩子我瞧着哪哪都好,人实诚,没啥心眼,年岁上又正好补足了这么多年我们不同岳家来往的谎言。”
赵二娘听得直点头,她也中意,长得高,还能吃。饭桌上她瞧得真真的,徐鹿鸣一口气喝了三碗汤,吃了五碗饭,要不是顾及脸面,估计还能塞下两碗饭,一碗汤。
能吃是福,能吃这么多,有大福!
“就是有一点不好。”
“他家在西北,要真跟咱家木兰成亲,咱木兰可就要跟着他去西北了。”
刚在饭桌上,徐鹿鸣从姜父这儿套了不少姜家消息,同样姜父也把徐鹿鸣给了解得差不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