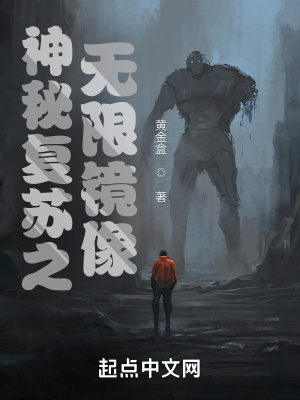倚天中文网>八零夫妻人生小记56章免费阅读 > 80-90(第15页)
80-90(第15页)
“互相帮忙嘛。”桂春生想得很开,让万云不必过分挂怀。
不过,周长城没忍住,还是问了:“桂老师,您怎么搬家了?”
这件事,说来其实很简单,桂春生几句话就说完了。
他和凌一韦本来是学校的老师,但十年运动之后回到学校,有几个人都不能重回岗位了,尤其是他们两个家属大多在海外的难兄难弟,恰好他们平反时,按照原先的情况,陆续都住回学校原先分配的家属楼去了。八十年代初,学校缺学生,也缺老师,更缺这种有社会资源的老师,学校为了与这批教师保持好关系,就以公家租赁的方式,把房子租给了他们。
但随着改革越来越开放,学校引进的老师也在逐渐增多,新的学校家属楼建设缓慢,总得要解决新进来老师的住房问题,就得让非正式的那批老师搬走,再把房子腾出来,这件事其实已经说了有几年了,但文件真正落实下来的还是在今年年后,周长城万云他们回平水县去没多久之后的一周。
随着学校慢慢开学,新老师要住进来,桂春生和凌一韦等人就得收拾东西搬走,这些事情,怎么往前牵扯,都是混乱的,桂和凌两人都是单身寡人,年纪过了五十,没有儿女在旁,就懒得去起冲突,跟学校协商多住一个月才搬走。
这珠贝村的房子,其实是八零年时,当地发还给桂春生的,但桂春生一直放租给来广州打工的外地人,恰好过了年,那十几个人集体撤走,不知道是否回自己老家去了,他和凌一韦找了收破烂的人来收走那些架子床,几乎丢掉所有东西,才清理出来四间房。
“人到中年,搬家一次,真是要了老命。”桂春生抚着自己的腰,难怪老人家都不爱挪窝。
周长城和万云却直道可惜:“要是我们早来一个月,桂老师就不必这样辛苦。”
桂春生却摇手:“我们都是花钱叫了人来搬家的,”甚至有两个下属也来帮忙了,“但很多事情非得自己亲手去做,才能摆得符合自己的习惯,他人替代不了。”
周长城和万云这才不说话了。
说了房子的事情,话题兜兜转转,又回到了周长城找工作的事情上,他们两个现在还没想清楚,究竟是要找提供宿舍的工厂,还是在外头租房子住。小两口自从结婚以来,还未分开住过,又是刚到广州的陌生当口,自然是希望住在一起的,因此对未知的未来一片茫然。
桂春生则是让他们先放心住着,仔细问了周长城几句他会做的事情,心里有数:“这样,既来之则安之,在我那儿先住着,不必着急搬走。吃过饭你们逛一逛再回去,回去后,辛劳你们一场,把房子里的卫生搞搞干净。明早再过来医院,我先给技术学校的朋友打个电话,他们是专门培训电工和技工的,问问他们那边还要不要人。”
桂春生浸淫教育文化界多年,桃李满天下说不上,不过相熟的人大多在报社,要不就是在学校,托托人,总是能打探到消息的。进工厂太吃苦,他也想给周长城找个相对轻松的活儿。
周长城自然是千万个好,对桂老师拍胸脯:“桂老师您放心,家里我们一定顾得好好的。”
“那就好!”桂春生笑眯眯的,只觉得这个春末不似以往寂寞。
把桂春生送回医院病房后,周长城和万云在四周走了一圈,不如过年时的那种新鲜和好奇,只觉得这里四月的天,热得出奇,似乎长裤已经穿不住了,他们也没有在外面待太久,而是回珠贝村打扫卫生去了。
下午,凌一韦办好了自己的事情,骑车去看桂春生这个老同学。
桂春生刚刚送走两个来汇报工作,找他签字的下属,洗洗手,门口就响起了凌一韦的敲门声。
“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?”桂春生让人进来,也不和他寒暄,直接拿出一个陶瓷杯,洗干净,给凌一韦倒茶喝。
凌一韦接过来,笑:“今天还算有进展,正在进入下一关了,办事员跟我讲,等和我的单位核查完这几年的工作情况后,就能到拿长期探亲护照的那一步。估计还要一个多月。”
桂春生坐在病房里的一张藤椅上,慢慢地喝茶,半晌没说话。
“春生,你真不打算出去了?”凌一韦都记不得自己是第几次问桂春生这句话了。
“不去了,我现在不是好好的。出去了,又要说一遍姓资的,姓社的,人家也不一定认我的身份,我也实在懒得去吃这种苦头。”桂春生低着头,认真看着陶瓷杯里浮沉的茶叶,“倒是你,头几年不下决心,现在才下。”
凌一韦还是笑,拿着茶杯,一时间也有些恍惚,终究没有藏好那丝怨气:“好好的人,像个个过街老鼠,被人从这里赶到那里,哪里都不是我的家。”
桂春生的条件比凌一韦好些,至少有处可去,心态也更宽,可他也不想说什么了,说了句不那么应景的话:“有人辞官归故里,有人漏夜赶科场。”
凌一韦放下杯子,没有再说这些已经定下来的事情,反而说起周长城和万云,他大为感兴趣:“你这是从哪里找出来的一对年轻人?昨天我让他们进门,他们还不敢乱动,好在也不是喧哗吵闹的人。倒是对你很关心,一听说你在医院,恨不得马上要来看你。”
桂春生略为得意,对于周长城和万云这两人,是目前他看得最准的两个人了,就说了几句和周长城的渊源和其来广州的目的:“那女孩儿是他老婆,两人刚结婚一年,新婚燕尔呢。”
“你就让他们这样空手住进来?不怕请神容易送神难?”凌一韦这些年可见过不少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,提醒桂春生,“小心引火烧身,趁着火苗不大,让他们赶紧出去住才对。”
说起这个,桂春生倒是难得和凌一韦说起一些往事:“你记得吗?八二年开始的时候,我们那栋家属楼的老师们,几乎家家户户都捐助过一些学生。”
“记得。”凌一韦也帮助过两个偏远农村的学生,只是后来大家断了书信,再没有联系。